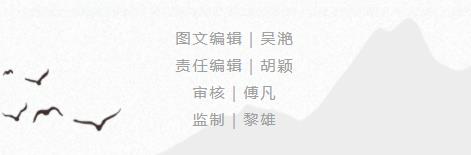作者:谭永西
又一次来到黄袍。又一次在硒泉边掬一把清甜的泉水,又一次在驿站口呼吸天地的清新,又一次站在华罗寨沐浴雄霸的古风,又一次在伐桂书院聆听遥远的书声,又一次在红豆杉下和应鸟儿清亮的歌喉,又一次在兰若寺静听远逝的晨钟,又一次在方琼像前追忆他拒敌的豪情,又一次在和风中品尝鲁直第富硒的农作物。

已记不清是多少次来黄袍了,还不说在黄袍工作的时日,就是工作调离后都无法理清来黄袍的次数。
我喜欢来黄袍,黄袍给过我太多独特的记忆。
还记得第一次来黄袍的情景,我怀着即将走上讲台的兴奋,从田东出发,向东而行,越过鲤港的青石板,穿过巍峨的八燕渡槽,眺过长虹卧波的南虹古桥,经过刘塘湖的故里到达夏家。在夏家一转角,随行的人告诉我,已经到了黄袍。抬眼一望,眼前的山头就给了我一个惊喜,那山犹如一只雄鹰。正前方的山头就是雄鹰的头,两边绵绵的山峰就是那伸展的翅膀,整个山脉就像是展翅的雄鹰。我在心里给这座山取个名字叫雄鹰山。上次几位外地朋友要我带他们逛黄袍,到这里我要他们观看山形,他们脱口而出:“好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”,也说出了与我一样的感受。当时我在心中悄悄许下心愿:“既然来这里当老师,就要尽我所能,把山里的孩子培养成雄鹰,让他们飞出大山,飞上天空。”一晃近四十年了,当年那些孩子有的是博导,有的是专家,有的是企业家,有的是艺术家;有的在建设家乡,有的在服务家乡,有的在宣传家乡;他们有的在黄袍服务乡邻,有的在县城发展,有的在省会立足,有的把经营带出了湖北,有的还把生意做出了国门。每关注到他们一个发奋图强的信息,心里总有甜丝丝的感觉:“又一只山鹰腾飞了。”虽说他们的成功得益于新时代的馈赠,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造化,但我也还是因为参与过他们成长的过程而不失自豪。

想起教书生涯,我的心里还真佩服自己初上讲台时的那股子傻劲,像个二愣子,不知“畏惧”二字是怎么写的,学校要我带啥课就带啥课,哪个课程缺人手就去上什么课,带学生练过太极,要他们柔中带刚;领过学生吼过劲歌,要他们“再也不能这样活”;引着学生画过朝阳,要他们记录世间的美好;给他们介绍过中华几千年的灿烂,与他们探讨过人生的意义;更多的是与他们探索物理的奥秘,化学的神奇,还有数学的简洁严谨。
教学之余,与孩子们也有无穷的乐趣,在大山里唱过笑过疯过。曾一起欣赏过白水岩那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壮观,领略华中第一瀑的气势;也曾在瀑布边探访“此洞连洞庭”的溶洞,感受造物主妙手天成的神奇;更在瀑布下小潭子里摸过化石,端详着几百几千万年前的古生物。曾一起站在润田大屋御敕史部匾下,感受读书人的荣光;也曾驻足在方琼庙前,感受读书人的担当。曾在黄菊妈的墓前肃立,感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;曾站在天潭堤上清醒,感受人定胜天发奋图强的魅力;也曾到黄家祠堂参拜,接受“元帅从这里起步”的熏陶。一起在山上摘过毛茸茸的猕猴桃,也一起在小溪里捉过横着走的石螃蟹。一起捡过甜津津的板栗,也一起掰过香喷喷的玉米;曾在润田的大银杏树下摘过扇叶,也曾在擂鼓坪那树干平伸于河面的弯脖子柳树下追过小鱼;曾在鹿叫山寻觅过麂影,也曾在华罗寨上遥望过洞庭。

来到黄袍山,自然忘不了小动物给我的惊喜。那些动物仿佛都有灵性,且不说机敏的黄老鼠,还有报喜的喜雀,也不说叽叽喳喳的鸟儿,还有那勤劳奉献的蜜蜂,她们时时给你欣喜。更奇的是几次与动物的邂逅,简直可写为传记。还记得一次农忙假后返校,走进房间,只见一条大蛇盘在床上。我心里紧张,就拿来长竹竿在蚊帐外敲打,它就乖巧地走了,再也没有来过。在那里还两次遇到过豹子。一次是周末,我出门上厕所,正在山沟边方便,一抬头,山沟对面正站立一只豹子,正面对面的看着我。那时不知是哪来的定力,我没有惊慌,看着她慢慢地往后退,一点一点地退回了房间。一次是周末,早上起床出门,远远望见一只豹子躺在对面食堂的石阶上。两次“惊吓”,事后却想不出它们有伤害我的举动。更有趣的是九七年的劳动节,我们几个老师正在学校聊天,一只麂从学校前的小溪里跃上岸头,越过校门,就直奔一个教师的厨房。我们几个大笑:“莫不是见我们工作劳累,上天特意送给我们的礼物”,那天我们都喝到了新鲜的麂肉汤。还有一次我们陪徐臻教授到黄袍,中午在黄袍山户外基地休息,两群大雁特来献舞,一群来表演一个圆阵,另一群就来个回旋,这群来个花式,另一群就来个阵法。上下翻滚,嘎嘎鸣声,争奇斗艳,精彩纷呈,足足表演了近半个小时,让人叹为观止。

多次到黄袍,清楚黄袍的变化,现在的黄袍越来越美了,是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,润田小学搬到了石丼,望湖竖起了新牌楼,高山上遍布了农家乐,元帅广场进驻了荻田村。甘下通了旅游路,别墅挤走了老民房。可不管黄袍怎么变,我对黄袍的山水还是情有独钟,因为那厚土下埋有我的亲人。一踏上黄袍的黑土,总能感受到他们热切的眼神。当年生活很不宽裕,爱人又要去蒲圻读书,家里的窘迫可想而知。岳母二话没说,就把两个孩子接上大埚。她一个农村老人,自己的日子过得也紧巴,现在既要带人,又要农作,还要纺棕绳换一点零花钱给孩子零用,就更艰难了。有一次我上大埚,发现了她把屁股顶在土墙上,手在纺着棕绳,孩子就睡在她背上。那一刻,我心疼了好久。
我对黄袍的山水有感情,不仅因为有亲情,还有与山水能相互理解的交情。还每当我有一点小小成就在心里嘚瑟,站在黄袍黑土地面前,那点点骄气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每年都在付出,奉献了无数的食粮,哺育了许多的子民,她说过吗?她夸耀过吗?生活中受了委屈无法诉说,站在黄袍的石头面前,那些委屈都云消雾散。那些黑石头虽没言说,可我一看就知道,那一道道皱痕,一定承受过成万上亿次浪花雨水的撞击,她说过自己的委屈吗?她流露过半丝不满吗?黄袍的山水还像朋友,什么心里话都可与她诉说,她从不讥笑挖苦。若疲惫了到石头上坐上半日,离开时还能还你一身轻松。
多次往返黄袍,一融入黄袍山水,我总忘不了李白的吟唱: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”;站立黄袍山头,有时兴来,会大声朗诵:“你见,或者不见我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。你念,或者不念我,情就在那里,不来不去。你爱,或者不爱我,爱就在那里,不增不减。你跟,或者不跟我,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,不舍不弃。来我怀里,或者,让我住进你的心里,默然相爱,寂静喜欢。”
2022年6月于通城